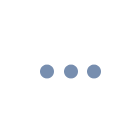75号 流云的声
壹
阿和坐在我飞驰的电动车上咬着我左肩时,并没有想象中的疼。
或许说,是因为从脸颊“咻咻”划过的风以及风里的小沙子太过痒而使我对他牙齿的用力反应迟钝。可,那天的风真的很痒哎,从林叶间隙穿梭过的太阳也温暖的恰到其实,街两旁的一排排小破商铺的额头上酥旧的塑料布招牌也让人心安,可不管怎么说,我的左肩上还是被他咬出了血痕。
我很生气,上次在车床那里我想要舔舔他耳朵的时候他还他奶奶的死活不肯呢,难道他以为我要强暴他吗?难道他以为我对他就像他对我一样冷酷又无情吗?
阿和是嫉妒我,那个坏种。
我知道他不喜欢甚至讨厌吴小姐。
是什么时候开始厌恶吴小姐的呢,我记不大清或者说在我潜意识里阿和对吴小姐一直是敌对的关系,但自从上次电话后这种真实的错觉就再也挥之不去了。
“家辉,你今早去哪了?”阿和在微信上问我,我没回。紧接着我的电话响起了,同时,房间里充满了他的声音,一前一后。
我连手机铃声都是他的语音。
“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难道你现在不方便?”阿和的声音软糯糯的,我突然警惕起来。
“我没看到嘛,刚下班回来累的要死那个能有力气爬起来看微信。”我狡辩道。
“真的?”
“真的真的。”
“何家辉你奶奶的放屁,你骗我你信不信我过来割了你?你信不信?呐?你信不信?我告诉你我卷起袖子就拿刀,你不要不信我!”阿和突然提高的嗓音让整个房间有种好笑的回声。
可我没有想笑,真的没有。
“我不会让你和吴小姐在一起的。”他声音里有种清晰的冷静,就像是做了重大决定似的。
“喂!你不要胡说什么,我和吴小姐什么也没有。你听见没!”
我听不见阿和的声音他好像消失在了电话的另一头,没有按挂断键就消失了声音。
“我告诉你不要胡来,你不要找她的麻烦,你听见没有阿,王八蛋!”
许久之后我看着手机显示的“正在通话”心里不由的开始担心,我在担心什么呢,吴小姐吗?我不知道。
人会突然害怕承认,害怕承认后自己所担忧的事物难以承担,害怕吴小姐遇见阿和。
可是,我到底喜不喜欢吴小姐呢。阿和怎么会突然提起吴小姐呢。
凌晨四点我在马桶上用力时我总结出了一个答案,是因为吴小姐太漂亮了吧,不,这里应该用“美丽”这个词。或许用“咯噔咯噔的在心尖上,在掌心在脚底板划来划去”更准确呐。
在通话之后就再也没见阿和提起吴小姐了,因为我已经快两个礼拜没见过阿和了。
心里虽然惦记着阿和但与此同时时时缠绕心头的却多了另外一个人的影子。当我想要尝试衡量这两个心事谁更胜一筹时却很惭愧的发现我没有找到可以拿来衡量的方法和标准。说到底,心里还是惦记着他。
当我从颜料厂下班在职工卫生间洗手时放在水池旁的手机轻声震响,备注“糖先生”的短信弹幕在屏。
“在红星广场等你。请一定要来。”
我盯着短信,之前上班时思量的要去看望阿和的计划像浴盆底的活动圆塞,慢慢的被糖先生的这条短信淹没,沉浸在下,成了死塞。
贰
“喂,应该是红色吧。”
房间虽然很狭小而且到处是胡乱堆弃的素描纸和廉价盗版小说但阿和的声音依旧很清晰。就跟我晚饭在厨房油蹦的洋芋片一样,想起来干脆有又让人期待。
“喂,是红色啦,我告诉你如果是画画的画就应该是用红色的,难道你不懂最让男人刺激和拥有的就是红色吗?我告诉你你听我的准没错你不要胡画啦。”
“和耀生你明天把你的嘴用厂里的车床轧紧,画大白天的天空谁会用红色,红个鬼阿。”我没停下手上的笔刷,小心翼翼的修着画里女人的蓝色连衣裙。
阿和还在我身后的沙发上说着什么我却没心思理会,心里盘算着秋后的十月,北安美术学院成人特招的日子。盘算着努力了4年,这次能不能考上。
说来,对于这个我意识之外有肉有乳的社会现实,我始终隐瞒着自己的秘密。或者说保卫着它。其实我知道我周围的很多人也有着隐秘,和我一起上班的颜料厂的李老头有,颜料厂的厂长那个总克扣加班费的黄老板有,吴小姐以及阿和,我周围的所有人都有。这并不是文艺的猜测,是他们脸上终年挂着的雾气所展露出的。
而我,而我的隐秘除了和阿和是情人外,再有的就是油画了。我寄希望于那个所谓的成人自招,用一幅画博得主考官的眼睛,然后堂而皇之的离开这。
阿和并不知道我会离开,因为,我画的天空是蓝色不是红色。嗯?
“喂,我说”阿和跳下沙发,穿着漏眼的运动鞋的脚拨弄着我靠绿皮沙发旁堆弃的矿泉水瓶,道“你们厂的黄扒皮不知道你在偷料?”
“厂长不会每天都下车间查看的。”
“那总有万有一失的时候吧?”他说着从夹克里摸出盒兰州咬起一根来。
“有,但现在还没有,这就行了。”我回过头道。
“打火机在木桌下面的横档上。”我冲他道,“还有,去烟台抽我又不是吸油烟机能把尼古拉排出去。”
阿和转身去烟台的时候碰掉了用矿泉水瓶做的简陋颜料罐。五颜六色的塑料瓶在地板上滚向四周,像洒了一把珍珠。
一个礼拜有两次我会带个包里面装满了空塑料瓶,当回来时原本空虚的背包就会变的死沉。县城里的文体店专业油画料忒贵,虽然厂里的油料总是发干和气味刺鼻,但起码不用花钱。
这些五颜六色的瓶子此刻就散落在我的脑容,阿和趴在阳台看着夜景,即使这整个县城并没有什么好看的。
“这个世界又有什么好看的呢?”
“家辉呐,和我去骑车。”阿和背对着阳台,星夜在其后像是专设的巨大帷幕。我竟然嫉妒起来。
“去哪?又没有什么好去的。”我没好气道。
阿和停顿了一会,好像是一分钟还是两分钟。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暴雷突灭的间隙感觉让我觉得嗓子发干,让我脱水。
“带你去个地方,漂亮的不成样子的去处。”他说。
五月份的风不大但还是清凉地让人冷静。街道上半明半暗的塑料灯箱被我破烂的电动车缓慢甩过,像要征服沙漠的勇士把身上的累赘一件件遗弃。我知道阿和和我一样想把这个容我们安身又牢缚我们的县城遗弃。可,那我们去哪呢?
“家辉阿,你屁股变大了阿,上次和你在你家时它还很合适么。”
“妈了个鸭蛋,是你才对吧!”我嚷嚷。
“你不用往后挪阿,你往前紧紧,我容许你的屁股变大。哈哈哈,不不,应该是我命令你让它好好的发展唔。”阿和单手捏把一只手还象征性的反向侵袭。
“要多吃鸡蛋阿,听见没有?”他又说的严肃起来。真是的。
电动车上又爆发出和耀生粗糙又大胆的淫笑。街道上的三三两两纷纷侧目,简直是臊死人。可,内心却是变的通透畅快起来,融在阿和的笑声里看到的却是油画里的贝加尔湖。是新疆的天山。真奇怪呵。
后来等我离开之后在去往另外一个城市的途中,躺在国道旅馆里的我才发现原来当初的种种是那个样子,才发现我一直逃避又依附的感情是真实的喜欢。
哎,便是如此吗。可惜当初的我并不知道。
“到了”他说。
我环顾黑色的四周,又睁大狗眼看清黑色中的建筑物。
最后,我在这个星光满天的夜里,回想着丢下画板放弃享受难得黄老板一个月里放的一天“懒觉假”,和阿和骑起电动在县城的马路描绘出一帧帧堪比奥斯卡的电影镜头。思此,最后又确认了坐在夜色中的那半栋建筑,回过头我满目深情的对阿和说:
“和耀生,你大爷的。”
叁
红星广场上的人很多,因为学校放假的原因。广场中心那块很吵,似乎发生了打斗的样子,远远的看过去是一撮一撮的中老年妇女围成一个圈囚住那些滑旱冰鞋和玩滑板的学生。这样的事不用打听看一眼就明了了。
两拨弱势群体争斗在一起谁胜谁负很难说,不过如果这时候有人站出来并组织一个投票大会的话我一定投给那些身处包围圈的学生们。因为我只听说过年轻人自杀没听过老年人自杀,为了给社会青少年自杀率做出贡献我一定投给那些美丽又脆弱的女孩们。
“何家辉?”
“到!”人群中我被自己吓了一跳。
“等了很久了吧,真是抱歉。”吴小姐不好意思的笑了。
“你还没吃饭吧?”
“阿,是刚下班不过不太饿啦,你呢?”我和吴小姐边走边说。
对面的路口恰时的亮起红灯。
“去吃饭?”她侧脸问道。
“好啊好啊,吃米吃面呢?”
“都想吃阿,怎么选嘞。”她用手指把短发往耳后撩拨过去,笑嘻嘻的说:“掷硬币吧!”
“那就吃面。”我说。
“不掷了?”
“掷过了”
“胡说也不打草稿嘞”吴小姐白了我一眼“什么时候?硬币隐身啦?”
我从她粉色的连帽衫里用食指夹出一个反面朝上的硬币捏在手心。
“正面字反面花那你猜是花是字?”我故作神秘。
“字!”
我把手掌展开手心里躺着的一圆硬币,是字。
“你赢啦,那好我们去吃面。”
绿灯亮了,过斑马线时她甩过脸嘟嘴又假装自然地款住我胳膊。我就是忍住没笑。
30岁女人嘟嘴的样子肯定可好看了。
吴小姐的手比起脸来已经略显痕迹。话说,从四月份的清明算起我已经好久没见吴小姐了。
吴小姐离婚已经快三年了,但我反而觉得她越来越年轻了,起码,皮肤越来越好了。她身材高挑性格又好典型的贤妻良母型,而且工作稳定薪水高活计少,每天按时打卡上班下班推死日子。但听说有好几桩求爱都拒绝了。
我个人觉得她拒绝的好,拒绝的妙,这样想虽然道德上对吴小姐是自私的但内心还是窃喜着。
“到啦,就这吧。”吴小姐说着拉我直径而入。
我抬头瞥了眼,招牌是“红星面馆”。很便宜的一家面馆。
其实红星县这个边疆小县城很奇怪,县医院我们叫红星医院,阿和做工的那家汽修零配件厂叫红星配件厂,连吴小姐做柜员的邮政银行我们前缀也加个红星,好像“红星”这两个字受用到可以成为这个小县城的所有厂牌名前缀。相比起来我上班的那个油料厂就叫“旺财油料加工制造厂”。
如果说黄老板这个无底洞加班和克扣加班费的王八蛋有一点点教人不骂娘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厂子不叫“红星油料加工制造厂”,即使“旺财”这个名字狗了点。
“家辉,我出来可没带钱啊,你要请我。”吴小姐打趣道。话音酥甜的像小鸟依人,邻座的几桌有目光投射过来,仿佛是安检的扫描仪一样,要把吴小姐看透明似的从头扫到尾。
她笑着朝里面厨房里喊道“两碗加面多加酱和辣椒!”
“吴小姐不用担心保持身材吗?不怕辣吃多了痘痘爆一脸吗?”
“以前怕现在不怕了。”
“说起来,还嫌弃自己的小腹太平坦想要一个圆圆的小肚子。你不觉得长了身圆圆肚皮的女人更好看?”
“诺,吴小姐真是奇怪阿。走在马路上这样说怕是有许多女人分分钟用眼睛刀剐了你的肚皮嘞。”
吴小姐轻快的笑了一声,像四月的风吹过挂在走廊柱脊上的风铃。她喝了一大口玻璃杯中的水抬起两只圆圆的眼睛说,
“何先生有喜欢的人了?”
这问题来的突兀,我竟然不好意思到不敢平视她的眼睛,刚搭过纯的杯沿有对淡淡的梨花红唇印,我把羞涩的眼寄放在唇印上羞臊道,
“还没有呢,还没有能养活好自己呢,怎么会有女朋友?”
“脸红的厉害呀,来喝口水压压惊。”吴小姐把自己的杯子递过来,伸手取时明显的感觉到她手指的温凉。
“是因为第一次被人叫先生呐。”23岁的我心想。
“油画还有在画吗?”吴小姐转移话题道。
“啊,有的。五月初的时候就画完了一副。”
“是用来考试的吗?”吴小姐双肘支桌,一脸温柔的问“北安美术学院的招生是几号?”
“8月初。”我答到。
“把你手机给我。”
我递了过去,吴小姐她知道我会把画完的东西照进手机,之前是现在也是。她也知道我手机的密码。我有点忧郁的是吴小姐她比我自己都了解我,按逻辑她也知道我的一切,那,吴小姐她究竟知不知道和耀生呢?
我突然察觉自己的心有种强烈的好奇欲和过分的不安。像怕被妻子知道自己有小三,而且小三还是个男的。如果她知道她会怎么想呢?
吴小姐盯着手机屏简单搜索后整个人就钉在了手机上。半响又忽然嘴角上翘笑了起来。
一种忧伤到让人明媚的声音渗透出来,我慌了。
“家辉阿,你是喜欢我呢还是喜欢上我呢?”
仿佛拉面馆煮面的大锅上升腾的水气,我和吴小姐中间弥漫开水雾,这些雾气浓郁一个个水分子彼此拥抱在一起“吧嗒”一声砸落在桌面,砸落在我手机屏幕那张全幅蓝色的油画上,砸落在蓝色天空中蓝色连衣裙的蓝色女人上。
看清楚了,是泪。滴滴,滴滴滴。
“面好嘞噢!”里堂厨房里捞面师傅唱歌似的嗓子,救命的声音。
吴小姐那天一直在掉泪,可她并没有哭,也没有说什么忧伤的话,她和我一直说说笑笑甚至给我讲个一个黄段子。可她的眼泪就是一直掉,眼睛逐渐红肿,她却一直笑的样子比梨花带雨还要带雨,仿佛下白雨的时候天空中依旧明亮的太阳。
我说,我没说话。我直接伸手给吴小姐搽干了眼泪,可刚一离手吴小姐那两口汪泉又荡漾出泪花。
吴小姐也不拒绝我。
我说,吴小姐你不要哭了。
吴小姐就真不哭了。她大口大口的吞面,嘴里还嚼着面条又给我讲起她小时候和她奶奶在一起的事,讲起她离婚后想去前夫家看儿子被婆婆给打出来并泼了一头屎尿的事,讲起那天和我滚床单的事。
突然有种保护欲操纵了我不堪的肉体要我起身抱住吴小姐,或者给拍拍她肩头说,没事了回家吧。的这种念头。
可我没有。
吴小姐站起身走出面馆我生怕有意外,连忙追上。在又一次回到那条绿灯28秒的斑马线上时吴小姐再一次自然而然的握住我的手。握的很紧。
肆
“和耀生,你大爷的。”我骂道。
“这不是你家吗?”
阿和仿佛没听见我的碎嘴,把小电动放好就开锁进屋了。没法子,我跟了进去。
阿和进去后熟练的从一堆螺帽螺丝刀中摸出一台矿灯,带提拉环的那种。冲我说了句跟上就转角走到房后去了。
阿和的房子是危房。但奇怪一直不倒。他家的房子有三层,是七年前政府拆迁工作的遗腹子。拆迁队在夜里拆了阿和家的老房子,阿和他老爹起夜的时候不幸被厕所房梁上的一根木椽砸进了茅坑没能爬出来。
后来政府也知道闹出了人命不得了,怕阿和为父报仇,许诺下给阿和赔偿一百二十万,让阿和对外就说他爹是前半夜掉进了茅坑后半夜拆迁队才拆了房子。政府鉴于阿和家贫困户补贴二十万。
阿和他爹的丧葬费也是政府包办。后来,又给阿和上了低保。当时阿和高中还没毕业,又许诺如果阿和考上了大学政府就供,考不上就给他找个稳定的工作。这样,才把这件死亡事件抹过去,让它成为了历史,成为了红星县的野史。
当时十九岁的阿和愣是让县政府开出了欠条。把许诺的种种都白纸黑字的印了下来。上面密密麻麻的印满了公章。从村里到市里,整整就九个公章。
再后来阿和就住进了这栋当时要拆未拆的房子。正好给阿和做了家。
阿和打开矿灯塞给我,示意我举着。然后向前一跨面向了我。
“喂,何家辉,你看得见我身后吗?”
“搞什么嘛?大半夜的把我拉到这里,看黄金啊看。”我嘟囔道,说着便左手摸索矿灯的开关,想照亮周围的世界。
“你身后藏着奥特曼?”
“吧!”
灯亮,世界显。
我看见一个披着军绿色防水布的怪物立在阿和身后。
“怎样?”阿和盯着我的眼睛道。
“什么怎样?”
“你知道我身后放着的是什么不?”
我感觉到在阿和声音中存在少有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让我着迷也让我好奇。从他之前那个放浪的喉管中出现一种自豪,对,就是这种让人讨厌又着迷的自豪骄傲。
“难道是只母奥特曼?”我严肃道。
“哈哈哈哈,哈。”
“家辉,把矿灯放在你前面的那棵树杈上。”阿和吩咐道。
“嗯?怎么。”
“把手机的闪光灯打开。”
“好了,到底做甚?阿?”
“不够,不够把灯光调到最大最亮!”阿和对我喊道。
“来,拿着举高点。”阿和从屁兜里掏出自己的手机并打开闪光灯来交付我左手,于是,在五月蚊鸣的夏夜,我像个精神病儿童一样双手高举向前照射前方。
与此同时,成团的蚊子在我周围打转,灯光所到之处尽是飞蚊。
我快要骂娘了。
可我并没有,因为下一刻我就被吓住了。
阿和在光明的照耀下像个斗牛士一样挺着腰神气的甩下防水布,一只高大威猛的四驱摩托车惊雷出现。流畅的机身和它在光下和阴影共同勾勒出性感线条,硕大的发动机自然而然的镶造在左侧机身下。连坐垫都是加宽的双人排坐。
我那娇羞且褴褛的粉红色小电动简直害臊到缩到墙角。
我几乎被黑色机壳反射的光亮瞎我的眼。
这妈妈了个咪的,真是比出现一只哥斯拉都惊喜意外酷炫霸拽。但很快我就反应过来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车很好阿,铁定花了万儿八千吧?”
“没花多少钱,只是发动机不好找,哎,想想就累死人。”阿和装x且认真道。
“咦?不是你买的?”
“买个鬼。你见过哪有这么好看的摩托。”
“真不是?你莫唬我,你不是在外面借钱买的?和耀生你给我说实话,你究竟借了多少债?”
“欠你个蛋欠,你不要老因为我上次借过债你就诬陷我。你剐掉你脑门下的有色眼睛好好看看!”阿和已经涨红了脸。我看的出那不是伪装,那是被我气的。
把手机塞给阿和后我走上前默默凝视这台摩托,她真的很漂亮。我用手指的指腹慢慢贴身划过她的身体像水面下的鱼用鱼鳍划过冰面。
阿和走过来把住车头说,你知道吗,我一直想去外面看一看,想看看红星县以外的地方。
“骑摩托吗?”我问。
“对,就我和他。”他瞅着红色摩托道。
“你钱够吗?以后呢?你回来之后呢?你厂里的工作你还能接到手吗?”
“呵,谁知道。”
“不过,不过我一定会走的,何家辉我走了你是不是要找其他男人?”阿和点了根烟胯在车身上质问我。
“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只能互相依靠,你个基佬你要等我回来啊,等我出去看看世面我就回来,回红星县和你过日子”他说。
“我不回来的。”我说。
“你能去哪?和我一起骑摩托?”
“8月初我要去北安。如果考上我就不回来了。”
阿和把烟头扔了,接着往地上唾了口烟痰,夜里起风风把他一头乱发吹地像吴小姐的裙带一样飘来飘去。
“你跟那个女人就算是上了床,就算是大了肚皮结了婚,你也休想摆脱我;就算是离开这里想逃的远远的,我也会骑着你现在看见的这辆摩托跟着你。我这辈子已经什么也没了,我不能和女人在一起不能生娃,咱们两个要是一个离了一个另一个就活不了。”
我仿佛有点不认识他了,草。
“何家辉,你他妈的在听我说话吗!”
和耀生在说什么我知道,可我希望我能告诉自己我不知道。
伍
我从没想过我会和吴小姐有第二次。我会第二次躺在吴小姐家的米色大床上。
“刚才你没带套?”吴小姐翻身盯着我下面问。
“好像是滑脱了。”我脸红道。
“可能吧,刚才确实很疼,估计是太用力的缘故。”
“那你怎么不叫停呢”
“可能是我太喜欢何先生很用力的样子吧。很有趣噢。”
吴小姐第一次教我做最后是哭出泪花子的,这次却全程在笑。
“那个,会怀孕吗?刚才套脱了。”
“你射进去了?”
“有一点,出来迟了”
“射就射了吧”她叹道。
“会怀孕吗?”我紧张道。
“有可能。”说完就笑。
我左手边巨大的玻璃没有拉帘,外面的阳光很好很刺眼,照射进来打到吴小姐的乳头上很好看,我用食指弹了一下,它会跳。
“果,你以后会再嫁一家么?”我问。
“不会了。”
“我活了三十三,该尝的都尝过了,我不想再吃了。管它甜的苦的我都不要了。”
“没孩子也行?”
“我给自己存了笔养老费,没大灾大难的话够给自己送终了。再生养么?哈,我养了条狗啦。”
“果以后会一直留在红星吗?”
“那还能去哪?”
“你不是说你以前大学是在上海读的吗?说上海女人穿旗袍好看的抵命,你不想再去上海看看?”
“看过了,够了,我知足了。”吴果爬过来亲了我一口,说,你呢?
“我就要走了。”
“几号?”
“3号的火车,凌晨的票。”我道。
我以为吴小姐还要说什么,可她什么也没有,我们两个就在被子掩盖下赤裸裸的躺靠在床。
“把你那幅画送我吧。”吴小姐笑了笑,注视着我努力让她的眼睛看起来活泼,“上次吃面我看见的那幅。”
“你画的真的很好家辉。”她肯定地说。
我有点害臊,心里从未有过的被人肯给的成就感和感激,好像在那一刻我看着吴小姐纯洁的脸仿佛在面对圣母玛利亚。我突然被吴小姐吸引了,像路过杂货店瞥见玻璃窗里的油画海报所着迷。
“留我这也是浪费,就送给果留做念想。”
“家辉你会回来么?”她问。
“不知道阿,也不知道能靠画画养活起自己么,在北安混的好的话就回来。”我认真答到。
“你以后要是还能回来,就来找我吧,你要是来找我我还没老透我就和你结婚。”
“就跟你啦!”她似少女般的笑到。
吴小姐把我的手放在她好看又好闻的乳房上,她的手指挥着我的手像是要我把她摸透似的。我手背上湿漉漉的,我感觉的到,闻的到,也明白,也不抬头。
心火翻卷,我突然跳起来坐在她的身上,我再次进入再次在吴小姐身上汲取我在阿和身体里从未感知过的欢快和被包裹的温暖。吴小姐死死的按紧我,她表情愉悦眼眶却湿润,那时候二十三岁的我只明确我被吴小姐神魂颠倒,并不理解一个三十三岁的女人静默流泪的原因。
她的眼泪和被红星县所包围的世界一样,是晒干了的精子的气味。
我和阿和没有任何告别只是给他微信了句“我已到站”,阿和开语音回了我让我自己小心。2秒长的语音里冒着哈欠,我猜他还在床上。
八月的红星县余温还是很热,仿佛夏天的脚太小一步胯不过秋天的门槛。仿佛我和吴小姐床后的余热还是滚烫。
检票的声音响在候车大厅时我正在看窗外,虽然时间还早但天已经放光,黑色变成了弥漫雾气的灰蒙蒙。考试桌上的评委们会喜欢这种颜色吗?谁管,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天将亮未亮,我和阿和骑我的小电动去买豆腐脑和小笼包。
十分钟后我坐在火车硬座上,看着绿色车厢一节一节离开红星。我不晓得明天,我只晓得当时天很蓝,我有烟,他有火。
阿和和他骑行的梦,吴小姐和她稳定的生活,还有我房间里和避孕套堆积在一起的被退回的画纸一沓一沓。就像随随便便在屏幕上食指摁下暂停。
我手机铃声突然响了。
“右边!看右边!”阿和在电话那头爆炸道。
我慌忙查找火车窗外,然后我看到了留在我生命中的景象。
阿和骑着他的红色四喷头摩托在铁轨右边的田地里一上一下的跳跃着,像胯着赤兔马,像个铠甲勇士。在愈来愈光明的天空下他迅速被火车超越,好像是我送别他一样越来越远,终于呼啸过窗框边消失不见,我知道他是走向了光明。
“王八蛋,一定要留在北安!”免提里和耀生这么跟我说。
该作品正在参加“我的青春有点料”全国征文大赛,长按识别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为这篇作品投票打call!
版权声明: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欢迎转发或分享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