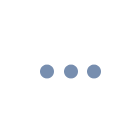90号 智齿
1
我曾经做过同一个梦好几回,细节不尽相同,到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只记住了大概,而且估计永远也不会忘掉了。
我的牙齿全掉了,不是一下子凭空消失,而是有一颗松动了,于是它慢慢的掉了,紧接着与它相邻的也开始松动,就像触发了多米诺骨牌,直到张开口变得像我奶奶一样。这个梦太真实了,真实到我能听到用手晃动牙齿时发出的“嗞嗞”的声音,感受到稍微带着些痛的快感,当它真正带着血迹掉落的时候,我竟然还有些释然与欣喜。每当进行到最后一颗牙齿时,我就会猛然的惊醒,满头大汗,赶紧把手伸进嘴里。我已经换过牙齿了,可为什么还会做这种梦?
夏天又长又黏热,那本三国演义已经被我翻得破烂不堪,我喜欢赵云,勇武英俊,我时常拿着棍子在院子里挥舞,想象自己置身于千军万马中。
棍子在石灰地上敲得脆响,震得另一端的手生疼。无须别人多说,我自己也是觉得不像的,我瘦弱不堪,还带着眼镜,不认识我的人觉得我是个知识分子,学习上进,将来肯定大有作为,可身边的人都说我这是看不好的东西看坏了眼,是报应。我一开始还跟他们急,后来也就看开了,眼镜这东西也不是太碍事。倘使赵云真的张我这样,那估计被人随便刺死于马下。
“你说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还整天看些不着四六的东西,干些不着四六的事。去把醋打满去。”我讨厌父母训我,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下不了力,像跟我一般大的文青,也就是隔壁家的孩子,每年都帮家里割麦子,掰棒子,干大大小小的活。他长得黝黑,很高,力气大的像头牛。我其实很好奇,像他这么一大老粗怎么取了这么一个名字。醋瓶子上黏糊糊的,我不讲究,拿起来就往外走。
到小卖部大约要走十几分钟的路,我走的慢慢悠悠,我不怕热,那些杨树似乎也不怕热,他们站的笔直,叶子深绿色,一个个都高出屋顶来,投在院子里,屋顶上斑斑点点些阴影。天空高的很,湛蓝色,没有一丝云彩。它总是那样宽阔无边,我时常幻想,什么时候天空能裂开一个大口子,给我看点不一样的东西,哪怕是在梦里也行。可每当我将这事说给别人听时,他们总一脸厌恶,说我不光眼睛坏了,脑子也坏了。
摘一束狗尾巴草叼在嘴里,吹着夏天发烫的风,我喜欢这种感觉。
“能不能先赊着啊,钱找不着了。”
“从上个礼拜起不就说不能赊账了吗,这赊的账就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啊!你像那张家老二,去年的账还没还呢!小姑娘我不是为难你,回家拿够了钱再来,东西先放这儿。”
这老板尖嘴猴腮,大家都说他长得像个猴子,四十多岁。年轻时好喝酒,没什么本事,也干不了力气活,这些都是我听别人说的。
“来回太耽搁时间了,你就再赊这一回行不行?”
“一回也不行!”老板没看姑娘,但口气很坚决。
我见过这个姑娘,跟我同岁,在一个学校上学。他长得得有一米七,肤色很白,脸上有些斑点,脑袋后面扎了一条长长的辫子,很是利索。我跟她很少说话,不,应该是从未说过话,我也很少见她与别人交流。她走路时腰板挺得很直,衣领与袖角都很干净。我觉得她与我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她应该是舞蹈家,音乐家,应该激情澎湃地高唱着新时代的凯歌,或者平静的写一封字迹好看的长信。可她如今却满脸通红的站在柜子前,手里提着和我一样的瓶子。
“我帮她付了吧。”我向老板说。
姑娘和老板同时看向我。她眼神里充满了惊讶。
“咱俩是同学,我见过你。”
“我也见过你,谢谢!”
“多大点事儿,”我贴近她的耳朵,轻轻的说,“你真好看!”
她的脸瞬间又涨红了起来,没说话,也没看我,低着头径直跑了出去。我不知道那时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也不知道是我表现得太过猥琐还是粗鲁,可我说出了心里话,我推了推镜片。
“钱半道上丢了,我得再去一趟。”我拿着空瓶子走回了家。
“你怎么不把自己丢了,什么事都干不好。”母亲都没抬头看我,依旧忙着手头里的事。“你要是把这钱自己藏起来了,你爹回来准饶不了你。”那只黑白花色的猫又在墙角吃着不知从哪里衔来的东西,我没抱过它,它也没挠过我。各自相安无事,可我总觉得它要比我自由。
母亲从未对我发过脾气,她似乎也从未发过脾气,她是个温和的人。他总说我“生不逢时”,这我也很无奈,我出生时正好赶上了计划生育,母亲为这事受了不少罪,罚钱自不必说,所以她总说我是一万多块钱买来的。主要是那个管计划生育的婆子,她拽着母亲的头发,呲着嘴,怒目圆睁。
“你个小贱人,要那么多狗崽子干什么!你知道超生你这一个,上头要怎么处罚么,咱们这儿拨款都没了!”她手臂青筋暴起,唾沫乱飞。她抬脚踹在母亲的肚子上,腿上;巴掌扇在母亲的脸上。
她很结实,我觉得她不像个女人,倒像个母猩猩。至于她说没说过那样的话,我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得知了,可她打过母亲,这是千真万确。
她笑起来嘴咧得很大,平日里总说些没羞没臊的话,这管计划生育的就是不一样,管住了别人的下半身,却放开了自己的嘴。我想极力去还原她羞辱母亲的场景,我为其编写的语言可能还是太过文雅,凭她那张嘴,估计要难听百倍。
我曾跑到过她的办公室跟前,趴在窗户下偷偷地往里面看,她躺在椅子里,茶缸放在桌子上还冒着热气,报纸盖在她脸上,我很纳闷,她难道也识字?我敲了敲玻璃,里面没有动静,于是我轻轻的退后,俯身抓起一块石头,奋力地扔了出去。
“这他妈谁啊!”
1996年,那年我十五岁。
2
六月份,麦子熟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黄色有些刺眼。镰刀磨得锋利,左手抓着麦子,右手用镰刀使劲一勒,声音脆响,割痕平整。
麦穗密实,在麦秆的顶端微微有些下垂。阳光刺在结实的身板上,无论男女,都被晒得黝黑,汗水顺着臂膀和下巴不停地往下流,母亲的草帽有些地方裂开了,我看不见她的眼睛,印象里她总弓着腰,不停地挥着镰刀,干活很麻利。被留在地里的短短的秸秆坚硬而又锋利,它们的一段深扎进土地里,怎么拔也拔不动,而另一端则黑洞洞的指向天空,那是它们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地方。
我也割过麦子,可父亲说我割起麦子来像姑娘绣花一样,又慢又不利索,再者是因为我被那锋利的秸秆划破过腿,于是每年我都在麦田边观望,为家里人送水和干粮。
站在路边杨树的阴影下,吹来的风似乎带着些许凉爽。
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左手里提着用蓝色碎花布包起来的干粮,右手提着两个水壶。她的腰板依旧挺得很直,阳光打在脸上显得她更白了。
我笑起来,用力地朝她挥手。
她也看见了我,不过又立刻将头转向一边,握紧了手里的蓝布,朝田埂走去。
我将挥舞的手放到了后脑勺上,看着她的黑布鞋一步步地踏在黄土上,我一直都在笑。
麦子割好后就开始了晾晒,空地上,院子里,公路上,都铺满了四方的金色补丁,我喜欢躺在那一片麦子里的感觉,总觉得我躺在了世世代代的希望之上,有人看到后总要赶我,说我挡住了麦子就晒不好了。
麦子晒干后变得紧缩而又坚硬,在经过碾磨后就变成了面粉。我吃了十几年的馒头,就是这些坚硬且有些发黑的东西。麦子长在地里,而我行走在路上;麦子动弹不了,而我可以肆意地奔跑。麦子带着它的金黄色流进了我的血液。那每年五月末的大片金色,既是希望,也是绝望。
3
收完麦子我就开学了,每天推着那破自行车沿着河边去镇上上学,学校也很破,像我的自行车一样,零零散散。除了少许槐树外,整片地区种的都是杨树,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我看着他们长了十几年,就像它们看着我从爬,到跑,再到戴上眼镜。
七月末的一天中午,我推着车子准备回家吃饭,刚把车子推出校门,就感觉有一只手在拽我的衣服。我转头,她左手抱着书,右手往兜里掏。
“这是欠你的钱,还给你。”
“不要紧的,你先拿着吧。”
“我不想欠别人的,在说我也不想和你再有交集。”
我很难过,伸手接过了钱。
“你喜欢看书吗?”她刚想转身,我叫住她。
“喜欢……你想干嘛?”
“借给你看啊”,“就当作咱们第一次认识好不好,我叫周天。”
“你这人真奇怪。”她小声嘀咕。
“牟怡。”
我不光觉得她长得好看,连名字都好听。
我借给了她巴金的《家》,钱钟书的《围城》,还有一本《屠格涅夫文集》。她还是说了声谢谢,声音依旧很轻,不过我觉得她不再生我的气了。我一路上骑得飞快,车子哗啦啦的直响,可我一点都听不到,我的心咚咚的直跳,感觉迎面吹来的风将我整个身子都洞穿了。
书都是当兵的大哥留给我的,他之前在县里的书店打过工。我已经不记得我翻过多少书了,它们有的印错了行,有的则是黑糊糊的像是墨晕染开了一般。书里有江南温婉的女子,有异国风情的趣事,还有家长里短的鸡毛小事。而我只有一副眼镜,一辆破自行车,一具瘦削的身体。可我从未停止过看书,这也导致我自然科学一窍不通,班主任也说我生不逢时,偏偏要去参加高考。好在父母早就对我没报指望,除了啰嗦,很少管我。
我的下巴开始冒出了短短的胡茬,最里面的牙齿也微微有些疼。母亲让我少吃糖,可我给忘了。
4
“没想到你还喜欢看书啊。”她又来还我东西了,不是钱,是书。
“学习不上进,再不找点乐子,那这一天天的该怎么过。”
“那你有没有想过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好像吸进了一块凝固的空气,刹那间要窒息,“外面的世界?”我心想。
“要不要一起走走?”我提议。
她点点头,这让我有些惊讶。
我们沿着河岸走,方向是她家的方向,一路上到底聊了些什么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只记住了她穿了蓝色的衣服,辫子扎得利索,而且她第一次冲我笑了,她笑起来可真好看。
那天我在水井旁的草丛里看见了一条蛇,黑红花色,大约有半米长,一动不动,头掩在草里。我也不敢上前,只稍稍侧了侧身子,想去看它掩在草里的那一段。那场景着实吓到了我。它死死的咬住了一只蛤蟆,没有吞食,只是咬着,而蛤蟆的肚子则涨得像个气球。我实在是不知其中缘由,于是认定那是一条剧毒无比的蛇,毒性大过癞蛤蟆百倍,想到这,我更不敢靠近了。
“你怕蛇么?”我问牟怡。
“怕”
“我也怕。”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想我要是条蛇该多好,所有人都怕我,最好长得凶猛一点。”
“那你会咬我么?”牟怡捂着嘴笑。
“第一个咬你。”
井里的水冰凉,透彻。而河里的水则被晒得发烫,风吹得杨树叶哗哗作响,河水缓缓地流着,它将会流进黄河,然后汇入大海。在岸边上牟怡问我是要做井水还是河水,我说我要做井水。
我与牟怡的熟络似乎有些莫名奇妙,我喜欢她,而且隐隐觉得她也喜欢我。我还是借书给她,而且我发现她还是挺能说话的。
天气炎热,我翘掉了下午的课,带了一个网子和玻璃罐子独自来到了田埂旁。一旁引水渠里的水不到膝盖深,里面有好多黑色的影子,那不是小鱼,而是蝌蚪,颜色深且头小的将来会变成青蛙,而颜色浅且头大的将来都会变成癞蛤蟆。
我捞了整整一罐子,大多都是头很大的,有时还会捞上来蚂蟥,它们会贴在我的腿上,划开一道口子,拼了命的往里钻,于是我就会立刻拿起鞋子,使劲的朝它拍去,一切方法都不好使,它们只怕鞋底,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生物。这里的水和河水一样,都被晒得很热。
“送给你个礼物。”我双手抱着罐子放在背后。
“什么东西?”
“活的。”
牟怡喜欢猫,我不喜欢,也不讨厌。
“你从哪里弄来的?”
“抓的!”
“抓的?”她肯定以为是猫。
我将罐子拿了出来,牟怡吓了一跳,身子向后倾了一下,“啊!”
“这什么东西?”
“蝌蚪。”它们在罐子里一点都不老实,而我在夕阳下又抱着这么一罐黑乎乎的东西。我看的出来,牟怡有些生气。
“你可真无聊。”
“你不喜欢?”我明知故问。
“你别跟着我了。”
“它们会变成呱呱叫的青蛙,然后戴上眼镜,借书给你看。”
“噗嗤”,牟怡笑了,她其实不知道我这一罐子将来大都是丑陋的癞蛤蟆。
二爷爷家的狗疯了,眼睛通红,见人就狂吠,于是他让我把狗给杀了。我是见不了刀刃的,更别提鲜红的血了。先把狗的嘴塞上,然后五花大绑,不是单单绑狗,还有一块大石头。狗的黑毛乱竖,头不停的晃动,我听得到它嘴里呜呜的声音,它的眼睛里仿佛充了血。连同那块石头,非常的沉。我将狗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朝西边的水坑骑去。
“噗通”一声,气泡升起,波纹由大到小再到消失。
我其实是很不想做这件事的,而且我一直在想倘若牟怡在她又会怎么想。当我正真告诉她时,她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其实治服那只狗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力气,它呲着牙,尖利无比,口水四溅。仿佛是被它咬到了,我的牙又开始疼了。
5
晚上橘黄色的灯让我昏昏欲睡,我丢掉课本,架起梯子,爬到屋顶上躺着看星星。灯还没有都熄灭,杨树的影子在夜晚狰狞无比。路旁的草在微弱的光里比路的颜色要深一些,时不时的有人骑车经过,车子哗哗的响,很好分辨。
牟怡说晚上要来找我,我躺在屋顶上静静地等着。夜晚的天空和白天很不一样,我觉得它更高了,且没有一点杂色。它不是静止的,虽然我无法证明,可我始终觉得它是一直在动的。倘若跨过这团粘稠的黑色,有同样的一双眼睛望向高远处,他也一定会有和我同样的想法。这团黑色也是有着巨大的活力的,它吞噬了大地上所有人的精力,使他们沉沉的睡去。我伸出手去触摸,可我觉得这双手也要被吞没了。
在我与这团黑暗挣扎的时候,好在牟怡来了。他走得依旧是那么挺拔,在夜色里让我都能一眼认出。我在屋顶上朝她挥手。她看见了我,微微一笑。
我扶住梯子,她很小心地爬上来,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在屋顶上。我们盘腿坐下,空气中有微弱的风。
她静静地看着天空,仿佛也像我一样开始了不着边际的幻想。可当她突然开口说话时,着实吓了我一跳。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
“鬼?”
“嗯,就是鬼。”
“你怕鬼吗?”
“我不怕,可我想不清楚。”
“反正我没见过鬼。”
“你说要是世上没有鬼,那桂子奶奶怎么突然就疯了。”
“那是让她儿子给气的。”
“才不是呢,原来都没事,大家都说她是让鬼上身了。”
牟怡脸上带着莫名的严肃,我有些想笑。
“你看了那么多书,学习了那么多科学知识,现在却问我有没有鬼,你这是封建迷信。”
“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人太脆弱了。”
我答不上来,只顾着望着天空发呆。
我把我关于天空的胡思乱想都告诉了牟怡,他也说我很奇怪,还说我不应该待在这里。我抓住她的手,指向天上闪闪发光的星星。那是我第一次握她的手。
棒子快要成熟,长着淡黄色的须子和乳白色的颗粒。外面包裹的叶子草绿色,纤维粗糙,有时不注意会划破手。棒子已经高过了我,但它们很脆弱,它们的杆里面疏松,可尝起来却是甜的,像甘蔗一般,我不喜欢吃,因为它们划破过我的嘴,我也不喜欢吃甘蔗。我总是容易弄伤自己,于是我开始考虑牟怡的那句话,“人有时候很脆弱。”
棒子种的密,想要从地里穿过,需要不停地扒开叶子。空气在里面好像迷了路,闷热而又粘稠。我想跳到河里去洗澡,一直不停地游,游到河的尽头,海里。我从未见过大海,书上说海跟天一样,是蓝色的,望不到边际,有时静的像一面镜子,有时暴躁的掀起巨大的浪。我问父亲,父亲说海是灰色的,吞掉了我的叔叔。我不知道该信谁,可我知道海是巨大无比的了,它吞掉了黄河,却没变成黄色。
6
我的牙齿疼的越来越厉害了,腮帮子已经微微肿了起来。十二月,裹着厚厚的棉袄,父亲带我到县里去拔牙。那颗牙齿长得甚是奇怪,斜着张,在口腔的最里面。医生给我打了麻药,然后拿一些金属的冰凉的器具在我嘴里进进出出,他具体是怎么做的,我全然不知道,只记得灯很亮,刺得我睁不开眼。
那颗牙被我拿了回来,不是很白,长得也很奇怪,我把它埋在了牟怡家旁的槐树下面。
过完年,,1999年四月份,父亲搬来了一台电视,我看到了牟怡口中的外面的世界,也知道了要跨入新的世纪了。我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体内跳跃一般,让我无法平静下来。我拿来一块红布,上面写了“拓新”二字,我将它披在身上,像是开拓新世界的勇士一般。
放学时间,我就披着那块布在操场上疯跑,我跑到太阳一点点落下来,也跑到喉咙里血腥味一点点浓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跑,可我就是无比的兴奋,仿佛只有这样不停地奔跑才能让我平息下来。我的心突突的跳着,那沸腾的鲜血一定比夕阳要红百倍。黄土在我脚下飞起来,沾染了我的衣服。好多的人围了过来,他们夹在历史的缝隙里,像我一样。我没有记住一张脸,他们有捂着嘴笑的,有捂着肚子笑的,还有扶着墙笑的。他们说我疯了。
“牟怡,我喜欢你!”
我跑不动了,趴在地上大喊。
一直到高考,牟怡都没再和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她体内也有和我一样的血液,可她冷静的像是一块冰。
牟怡要去远方了,而我哪里也没考上,我去车站送她,双手放在后面,抱着一个玻璃罐子。
我对她笑,她也对我笑。
我将罐子拿到前面,里面都是浅色的,头很大的蝌蚪。
牟怡甩了我一巴掌,可我清楚的看见她眼里噙着水花。
后来我才知道,那颗埋在牟怡家旁的牙齿叫做智齿。
该作品正在参加“我的青春有点料”全国征文大赛,长按识别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为这篇作品投票打call!
版权声明: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欢迎转发或分享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