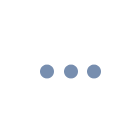81号 致木栾
拉上床帘,关灯,下铺,宿舍床是埋活死人的棺材。——楔子
3月10日。
我又浑浑噩噩过了一天,醒来时已经是午后了。混乱的生物钟让我还在恍惚之中,太阳穴微微胀疼。又做了一个冗长的梦,可惜我已记不起内容。只知道我的梦没有色彩,像一帧帧黑白镜画,很灰暗,很鲜活。
拉开窗帘,刺眼的阳光直射进来,我下意识眯起眼。窗外,能看见大片大片的栾树林和一小部分操场,零星几个男生在踢足球。栾树随风轻轻摇摆着,像吟游诗人轻声的耳语,在阳光下绿的要燃烧,三月的阳光很明亮,明亮的有些虚幻的错觉,带着温柔的风,像慢性毒药不知不觉渗入体内,一点点揭开长好的伤疤。可我却贪恋这种不真实感。
我的故事,只有玉兰知晓。
在我出生的年代家家户户刚从从平房搬进楼房没多久。在金刚水泥构建起来的城市森林里,我的玩伴是电视和一台老式收音机。上小学前我一直和外婆住,赶上计划生育,院子里和我同辈的孩子很少。我的左邻右舍基本是叔叔阿姨和大爷大妈们。每天开心的事情是午睡起来去院子里瞎跑看看大人们打牌,她们每次都会带好吃的给我。
可有一天,这样的日子被打破。原本属于我的零食在另一个小孩手里。那个小孩个头比我低半头,白白净净一双眼睛出奇的大,睫毛又密又长,阳光下头发是深栗色的。真好看啊,像妈妈送给我的洋娃娃。
那时的我已经有了审美,可是这个娃娃怎么不扎辫子,不穿裙子呢?我疑惑的问外婆,外婆哈哈笑起来说他是男孩子呀。“你骗人!她才不是呢,我嘟着嘴厉声狡辩,“男孩子不长这样而且男孩子比我高才对。”对面的孩子急了,皱紧眉头双手下意识的握拳迫切解释道:“我就是男孩子!”“我才不信,你怎么证明你是男孩子啊?”我歪着头自信满满的看向他,“我,我,我”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忽然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说道,“只有男生能主动亲女生的,因为女生会害羞,男子汉不会”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下给吓傻了哇哇大哭起来。
对面男孩子一时间也不知所措的说,“你别哭啊,我保护你,男子汉是要保护别人的像孙悟空一样可厉害了。”说着把手里的糖递给了我。我听到有大人的声音打趣说着,哈哈他俩多好啊,李嫂张嫂干脆定个娃娃亲。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想起来,但这个画面一直保留在我脑海深处以至于在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跑进我的梦里,像不甘心被遗忘似得来搅局。有时候大人们低估了孩子的记忆力,那些儿时的记忆是河流里涌动的暗礁,将长大后的自己拉近回忆的漩涡中,无法抽身。
从外婆口中知道,原来他是住在六楼李奶奶家的孙子。马上要上小学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又见面了。我们在栏杆上靠着,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木栾”“木栾?”我又重复一遍,真好听。“我的名字和一棵树同名,那是一颗会开花的树。”他骄傲的看着我,“好厉害啊”,我学着图画书里写的那样伸出手说,“真高兴认识你,以后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了”他开心的笑起来,眼睛亮闪闪的,也伸出手说,“你也是我的好朋友。”
从这时候开始,两个同样生活在城市森林里的小孩子他们手拉手,享受这属于童年时代的快乐。一个扎着小辫子皮肤黝黑的女孩跟在比她小半个头的漂亮男孩后面,在家属院里创造属于他们的秘密花园,直到夏日凉风袭来,外婆熬好绿豆汤,在窗边大声喊着回家吃饭。
后来我因为上小学,从外婆家搬走。只是偶尔周末空闲时间回去,很少能碰见木栾。好像什么也没有做,夏天就过去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时间就溜走了。一起分享的童年玩伴就像会丢弃的幼稚发夹,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轴上各自成长。
我再次和木栾相遇是在初二,在新高一录取名单中我看到了他。高一(8)班 木栾,记忆的洪流向我涌来......我喜欢听秋天干树叶落在地上被脚一踩的咔嚓声,某天我正在院子里玩的不亦乐乎听到身后传来同样清脆的声音,一回头发现是木栾,他朝着我笑的一脸阳光。那一瞬间这个笑容像是从亘古传来的钟声,在我内心回荡。
我们学校新生都在操场上军训,我假装初一新生偷溜进方阵里。在靠近国旗的那个方阵里,一个男生在人群中很亮眼,比那排的男生高出半个头,穿着白t和浅蓝色运动裤,和前排的人说着什么。还是小时候的模样,褪去了稚嫩,棱角更加分明。傍晚的阳光照向他深栗色的头发,身后是一整片的火烧云。
我好似又听到远处传来的钟声,带着零星的旧时光,在心头悄悄漏了一拍。
当某个形象刻进了记忆里,就会轻而易举的被寻找到,小心翼翼的躲避一个人要比不期而遇容易得多。之后的时间,我会在放学路上大波人群中一眼看到背着黑色书包的他,在全校升旗的周一看国旗队最右边的护旗手,在运动会高中组800米决赛中偷偷为他加油。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走上前去的勇气,是怕担心他记不起来我而失望?还是怕现在的我会抹灭他印象里我的样子?这些自我怀疑,这些留在青春里异样的小心思,谁也不知道。
可我最终也没遇见他。我清楚的记得那天阳光明媚,学院四楼的窗户里伸手就能碰见玉兰花的梦,还有记忆里只有花知晓的味道。
3月10日一场意外呼吸道花粉过敏带走了17岁的木栾。
那天教室闷热,我迷迷糊糊从课桌上起来,揉了揉眼睛。课间教室里人并不多,有些人在安静的写作业,有些人趴着午休,我后桌的几个女生围在一起聊着八卦。我抬头望向窗外,学校的玉兰花开了,像一朵朵白蝴蝶落在枝头,花瓣白的透彻,大片大片的舒展开,大方的露出棕黄色的花蕊。我静静的看出了神,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察一朵花,它花瓣上的每一条纹路,中间每一根竖起的细小花蕊。可我还是听到了,一字不差的刺入耳骨,声嘶力竭却又悄无声息的穿透耳膜。
“唉你们知道吗?昨天咱们学校国旗护卫队的一个人去世了,叫木栾。”“对对对,就是那个长的特别清爽又高又帅的那个”“好像是因为昨天下午他们打篮球,花粉过敏导致休克错过了最佳时间,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抢救不过来了......”
我考上C大,距离木栾去世已经五年。
学校有大片大片的栾树林,在翠绿的树叶中点缀着一簇一簇黄色红色的花,好似在时不时的提醒我想起一个名字。那个名字的主人我该怎么回忆他呢?只是童年一起玩耍的伙伴?懵懂青春里的暗恋对象?或是被仓促亲了一口的稚嫩男孩?穿着校服清秀帅气的学长?我自己也分不清。《蓝色大门》里孟克柔对小士说:“如果你的17岁,想的只是能不能上大学,不再是处男,尿尿可以是直线的话,你该是多么幸福的小朋友啊。我在想,一年后,三年后,五年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由于你善良又自在,你应该会更帅吧。于是我似乎看到多年以后,你站在一扇蓝色大门前,下午三点的阳光,你仍有几颗青春痘。你笑着,我跑向你问你好不好,你点点头。三年五年以后,甚至更久更久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呢?”
“虽然我闭着眼睛,也看不见自己,但我却可以看见你。”但我却可以看见你,木栾。依旧还是那个一笑很温暖追风似得大男孩,在不远处向我问好,走上前伸出手对我说:真巧,又遇见你了。
我很久没有撒丫子哭过,也没有什么事情让我真的开心。我不知道哪天因为记什么而忘关秒表,178个小时就这么毫无目的的流逝着。成长会磨平棱角带来麻木,以前迫切热爱的,笃定相信的,变成了无所谓不期待。
日子一天天平淡的过去,带走夏夜里的星空,十点过后的电影频道,言情文章里的男生女生,带走旧房子和外婆炖的汤,带走我跨不过的17岁。
一教楼前的玉兰花是三月里悄悄的梦。毫无征兆安静开放的同时就预示着死亡,一场微风就能带走一整枝芽。我的秘密也随玉兰花的凋谢被带走,被往昔岁月冲淡。人还是会不知不觉中就偏离小时候开的航道,驶向大人模样的彼岸。我还是不可爱的长大了。
该作品正在参加“我的青春有点料”全国征文大赛,长按识别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为这篇作品投票打call!
版权声明: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欢迎转发或分享至朋友圈。